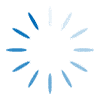纪栩吸吮着宴衡的手指,坚硬的指节破开娇嫩的软肉,只进去一半缓缓抽插,她像饥饿难耐时吃到珍馐却浅尝辄止,反被勾得花心收缩、淫水肆流。
她瞥过他胯下粗长凶猛的肉棒,咽了下口水,侧头道:“我有要事和你相商。”
顾忌到隔墙有耳,她用的几乎是气音。
宴衡似乎会意,却不以为然,他贴近她耳侧:“有什么事,明天再说不行吗?娘子,春宵一刻值千金,我们互相予取予求。”
他拔出手指,以灼热的巨物顶着她。
纪栩了然宴衡话中的意味,只要她使他今晚尽兴,无论她提什么要求,他明天都会答应。
可她怕待会儿圆房后她被他操昏过去,他明日起早办公,她可能会被纪绰送到庄子上观察是否受孕,即便她手里有藏红花能保证这回无碍,但她不在宴家的这段日子,宴衡和纪绰之间难保会出什么差池。
万一纪绰得知她在宴衡面前挑拨纪绰和温妪及主母的关系,疑心她要作祟,指不定纪绰会对她们母女做出什么事来。
纪栩深吸了口气,哪怕要败宴衡此时的兴致,她也不能错失良机。
她想了想,扭腰含住宴衡的龟头,碰上他错愕揶揄的眼神,她咬唇,斟酌着言辞道:“郎君,我昨日遵从母亲之命,把梅姨娘送回纪家,实则是另有主意。”
“我想请郎君出面,亲自将梅姨娘和我庶妹纪栩从纪家接来宴府,妹妹乖巧懂事,能替我侍奉姨娘,她也不会在府中生事的。”
纪栩寻思,纪绰和主母想要桎梏她和母亲,那她就以纪绰的名义,撺掇宴衡救她们逃出生天。那如何保证宴衡照做,不会因明日纪绰的反口而停手,她接下来还有后招。
宴衡见纪绰浑身肌肤白里透红、红中泛粉,整个人如经沸水淋浴,鬓发湿漉漉地散在枕上,眉眼间噙着难抑神色,娇软的躯体妖蛇一般在他身下拂来扭去,小穴紧紧地咬着龟头,恨不能吞入腹去……这副模样,显然被春药催情得极想索欢。
但她却竭力忍耐,樱粉的下唇被自个咬得失血泛青。
他知道她心善,一力在毒辣的母亲手下回护姨娘,还要处处避着院里母亲的眼线。但这些事情,她完全可以想个法子支开所有下人,或者日后去他院里详谈,每逢云雨之际,她都执意要和他议事,不免扫兴。
他往她口中填上一指,在穴里冲撞几下,故意道:“我上回问了两句你的庶妹,你又哭又怒,说我是想享娥皇女英这一齐人之福,我可不敢接她过来,省得日后你怀疑我和她哪朝有了一腿。”
纪栩被他插得身子颤抖、汁液流淌,花心空虚地缩动,却什么也吃不到。
她暗恨宴衡此刻的记性,但她们纪家姐妹共侍一夫的名声,她将来怕是洗不脱了,作为姐夫,他和妻妹前世今生颠鸾倒凤数回,他们早无清白可言。
她搪塞:“此一时、彼一时,我不会因小失大,请郎君往后明鉴。”
以宴衡的禀性,他们做尽情事,她不信他得知她身份后会不担责,至于纪绰会不会对夫君和庶妹暗度陈仓而恼羞成怒,这是她想看的一出好戏,甚至纪绰越表现得暴躁悲郁,她越感到兴奋刺激。
宴衡觉得她穴中如生尖牙利舌,死死咬缠着阳具不丢,深处似岩浆沸腾,迸溅的一股股热液淋得他腰眼发麻,叫他只想攻破阻碍、掠夺芳芬。
但瞧她神情一本正色,仿佛不是在与他床帏私语,而是厅堂论事一般,他不由窝火,面上却笑道:“若是我不答应呢?”强忍着紧致在穴里搅弄一圈,“你今晚是不是就不给我操了?”
纪栩见他笑容如明月映人,一双黑眸却蕴着寒霜般的冷意,恍若她要执意找他要个结果,或因此在床事上露出半分推拒之意,她体内能送她去仙境的肉棒,霎时就会变成一柄利剑,将她插死在床上,整晚别再想吐出一字。
她思忖着,环住他的脖颈,扭腰使两人下体嵌合得更深,待硬胀的龟头顶到脆弱的肉膜,她喘息道:“郎君净会与我开玩笑,你怎么会不答应。”
“你之前说,姨娘与你有缘,叫我们纪家好生待她,可纪家从来不是休养身心之地,我相信郎君,这回不会见死不救。好人做到底,菩萨渡众生,捎带我一个庶妹,对郎君而言,不过张口之劳,但对姨娘和我,却是雪中之炭,你怎么会忍心不帮我们。”
她亲他绷紧的下颌、滚动的喉结:“你给我喂了春药,今晚不操死我,那就是想折磨我……”
话音刚落,宴衡起身退出一些,注定她命令:“抱腿,低头,看着我是怎么插你的。”
历经两世,纪栩有些习惯宴衡在床事上的肆意妄为,但要她看着自己如何被他破处,她不禁觉得略微羞赧,忸怩片刻后,她抱着两腿膝弯放至胸前,望向两人交合处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